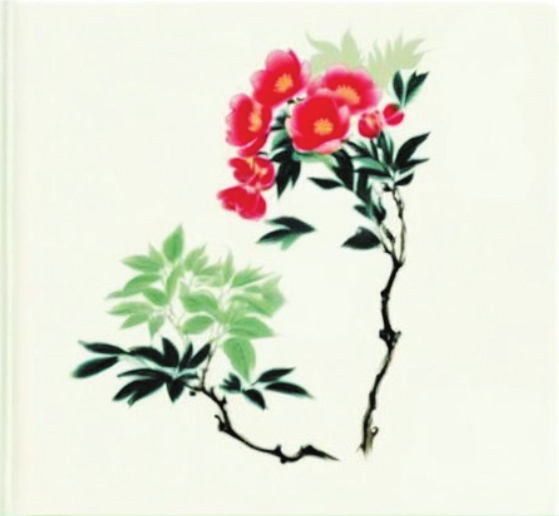他的笔下,无论是其间的一片叶,一根草,一株树,一条河流,一潭池水,甚至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语、一招一式,常常撒落一片温馨恬静,让我一往情深。
“山丹丹开花花又落,一年又一年……”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,多开一朵花就是多添一岁;树增一圈年轮,贝壳又多一道生长线。草木年华,人生世月,寸心皆知。
“枸杞头到处都有。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。”平常人自有平常人的幸福和希望。“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?”“槐花盛开,槐花又落了。”惹得一些寻常人家无由地失落和感喟。就是这平平常常的两三句话,汪曾祺立马写出了一个寻常人家的感情世界和生存天地。
真正是,无端地喜欢“人间草木”四个字。在现当代作家中,我想汪曾祺与我是靠得最近的一位。当然,这并不是我与他有什么零距离的亲密接触,或者个人的偏私,是他的作品让我感到那样的亲切,与寻常百姓家又是那般的熟谙,那些花鸟虫鱼,草木叶月,四季蔬果,四方食物,猪啊狗啊……尽是带着人间的情味,扑面而来,字里行间总是氤氲着一股人间烟火味,草木精神在。
说到汪曾祺,不能不说到他的父亲汪菊生。正是他这个绝顶聪明的父亲,给了他太多。父亲会画画,会刻章,能弹琵琶,拉得一手好胡琴,竹箫管笛,更是无一不通。还擅做风筝,做西瓜灯,养蟋蟀,看戏,唱曲……从小,父亲带着他高高兴兴地“玩”,多年父子成兄弟。这样,小小的汪曾祺,就有十八般武艺上身,终日里,吹拉弹唱,不歇片刻。有时,甚至还到田野里疯上一回,在一地金黄的油菜花里打滚。
上学了,汪曾祺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也是那样好奇和贪玩。看见那卖牛肉高粱酒的,卖卤豆腐干的,卖五香花生米的、芝麻灌香糖的,卖豆腐脑的,卖煮荸荠的,还有卖河鲜、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……他就久久地不肯离去,把那一街的色、香、味,嗅进肚里头,再在脑海里回味大半天。路过银匠店,他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;路过画匠店,他歪着脑袋看他们画“家神菩萨”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;路过竹厂,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,在火上烤弯,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……
后来,他在《戴车匠》中,便是这般生动描绘,美丽如画:戴车匠踩动踏板,执料就刀,镟刀轻轻地呻吟着,吐出细细的木花。木花如书带草,如韭菜叶,如蕃瓜瓤,有白的、浅黄的、粉红的、淡紫的,落在地面上,落在戴车匠的脚上,很好看。
很好看,很好玩,很有趣。世界,在他的眼里总是这样的新奇和有趣;人呢,一个个立在大地上,也是这般的平凡而有味。于是,汪曾祺就很喜欢写人。写“小明子牵牛,小英子踩水车;小英子的爸爸种田捕鱼,妈妈喂猪绣花……”;写一个小锡匠的爱情故事;写“李小龙的黄昏”;《熟藕》里的刘小红和卖藕的王老汉,《珠子灯》里的孙小姐;还有那《故里三陈》,那《钓人的孩子》,《辜家豆腐店的女儿》中的女儿,《黄开榜的一家》中的一家人……甚至包括改编古代故事中的人物——蛐蛐、瑞云、陆判、螺蛳姑娘……他总是“感觉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”,他自然而然地“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”,“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”。
当然,也写“为团长的老婆接生,反挨背后一枪而送命的陈小手”;“有既是水果贩子又是鉴赏家,死后和画合葬的叶三”;《兽医》里写了一位身怀绝技,外号叫做“姚六针”的兽医姚有多和寡妇顺子妈面对的一场喜事抑或丧事;《露水》中的一对露水夫妻的寒凉;还有那不绝如缕忧伤的《天鹅》曲……这样的人物和故事,更是让人唏嘘不已。
秦少游有诗:“菰蒲深处疑无地,忽有人家笑语声。”家长里短,汪曾祺信手拈来,皆成故事和画卷。家常小菜,汪先生写得津津有味,色香味俱全。故乡的食物和野菜,五味萝卜,四方食事,手把羊肉,寻常茶话,令人口舌生津,食指大动。人间草木,处处有情;花鸟虫鱼,个个生动。该独放时独放,热烈时热烈,安静时安静,自由自在,安闲自若,自得其乐。就像汪曾祺,这个在胡同口闲庭信步的慈眉善目的老头儿,亲切,家常,真实,温暖。须知,这个平和老头儿跳动着的始终是一颗温热的心。
我读汪曾祺的作品,读到九月的果园“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,宁静、幸福,而慵懒”,就是在他奉命画出的一套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里。他画一个整薯,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,画完了,薯块就再无用处,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,烤烤,热腾腾的,香喷喷的,吃掉。大多数时候,他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,观鱼游虾戏,听流水潺潺,悠悠地哼唱着小曲……他的笔下,无论是其间的一片叶,一根草,一株树,一条河流,一潭池水,甚至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语、一招一式,常常撒落一片温馨恬静,让我一往情深。我总觉得,有无边无际的阳光温暖着我,无边无际的温暖包围着我,十分美好。
汪曾祺多写童年、故乡,写凡人小事,想必他是发现了自己身边的“凡人小事”之美。美在身边,美在本分,美在质朴,美在心灵。许是原汁原味的“本色艺术”或“绿色艺术”,方能创造真境界,传达真感情,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。他也记乡情民俗,谈花鸟虫鱼。他爱好书画,乐谈饮食、茶话和医道,他记菜谱,谈掌故,写“野史”,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。大家知道,久演不衰的样板戏《沙家浜》,就是他写的经典唱词。
汪曾祺的本性中既有深深的草木根,也有较深的文人气。他在给《戏联选萃》一书所作的序中,颇欣赏贵阳江南会馆戏台前的一副对联:“花深深,柳阴阴,听隔院声歌,且凉凉去;月浅浅,风翦翦,数高楼更鼓,好缓缓归。”四十年后,他还是不忘昆明的雨天,曾写了一首诗送给朱德熙:“莲花池外少行人,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,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装裱好,挂在墙上。斯人已去,湿甸甸中的香气,触手可及。
人兴则草木兴,水长若日月长。有一个读者在读过我的乡村散文后,曾作如是感叹:这些隐在乡村杂木中的佳木和花朵,被作者轻轻地举过头顶,向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展示美丽。生活一词,在这里很淡很诗意,淡到若有若无,浅到清纯见底。作者的笔落在乡间,乡间不开花也难呀!我当然知道,于我是愧领了,说汪老则是吻合了。
汪曾祺为文从艺,向来随心所欲,随遇而安,随随便便。他向青年作者谈起文学来,也是拉家常一般,冲淡,平和,风趣。他说:“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,而是和谐。”他还说,无技巧便是最大的技巧,无结构便是最好的结构。他尤其向往苏轼的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,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。他也特别看重语言,他说“语言像树,枝干内部液叶流转,一枝摇,百叶摇。语言像水,是不能切割的”。他的语言是干净的,干净到不能增一字,亦不能减一字。他的语言更是有音乐节奏的,抑扬顿挫,如歌行板。
汪曾祺就是这样,一边写着素淡文章,一边喝着浓浓的烈酒。这种状态,旁人往往是无法体会的,我却深知个中三昧。“巴根草,绿茵茵,唱个唱,把狗听。”“牵牛花短命。早晨沾露才开,午时即已萎谢。秋葵也命薄。瓣淡黄,白心,心外有紫晕。风吹薄瓣,楚楚可怜。”悠悠人间草木情,道尽世间沧桑。浓淡两相宜,愈浓时愈淡。有道是:墨愈淡处偏成浓,色到真时欲化云。正是这样,有人评论汪曾祺的小说:“初读似水,再读似酒”。
他的最后一篇遗稿,是为未完成的《旅食集》写的题记。他在这篇题记的末尾中写道:“活着多好呀。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:活着多好呀!”是的,活着是高高的山,是长长的水,是开不败的花朵,是盛长的草木,是纯净的阳光,是清新的空气,是天上的白云,是地上的泥土,是和谐的世界。
这时,我倏忽想起他的《葡萄月令》里的一段话:“一月,下大雪。/雪静静地下着,果园一片白。听不到一点声音。/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”。
世界无声,天地皆白,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……
周伟